
 黄康俊 著《热带岛》(长篇小说)、《南中国海佬》(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4年
黄康俊 著《热带岛》(长篇小说)、《南中国海佬》(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4年
☐文 能
想闯入黄康俊创造的艺术世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虽然你很容易被他笔下那波诡浪谲,辽阔悠远的大海所吸引,为那些豪放不羁,技艺超群的海佬的性格和劳作所打动,但你想真正读懂他的小说,穿透层层迷雾洞悉隐匿在种种具象描写背后的小说题旨,破译种种文化代码所包容的文化蕴涵就不那么容易了。大海作为黄康俊小说叙事话语的恒常背景,只是为其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空间,要想真正读懂黄康俊的小说,你必须抛弃你以往那一套一成不变的阅读经验,从了解南中国这片处于历史嬗变过程中的热带海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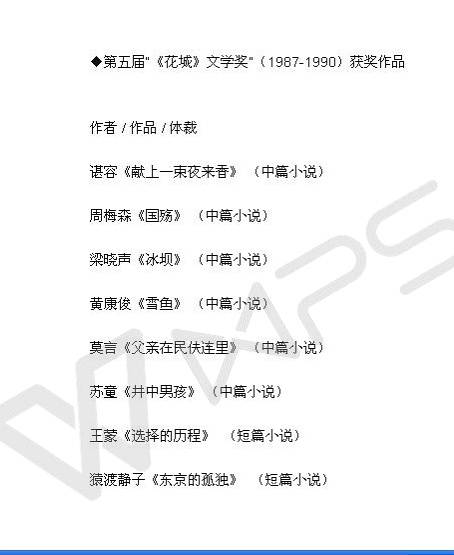
黄康俊的小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小说,一种海洋文化的韵味弥漫在他的这些小说中,这是黄康俊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前些年,我曾感叹广东这么一个拥有全国最漫长海岸线的省份,竟然没有表现海洋文化的作品,黄康俊的小说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康拉德、海明威等大师描写大海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业已成为经典;在中国文坛上,前些年邓刚《迷人的海》也曾倾倒了全国无数读者,相比之下,黄康俊笔下南中国的这片热带海域虽没有那雄浑苍凉,却更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兼容性,在时下失去了“轰动效应”的文坛,它无法引起像《迷人的海》那样的震动,但它具有无法取代的文化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邓刚笔下新老海碰子们对大海的征服与索取,表现了人类要征服自然的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表现了人和自然的一种对峙,而这种进取与对峙,却更多地保留了人类农耕文化时期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粗浅认识;黄康俊小说中的大海,表明的却是一种新的文化韵味,在这里人与海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无言的承诺,在这条环环相扣的生物链上,任何一个环节的损坏与脱离,都会危及整体的生存而导致链条的断裂。在《蟹岛》(中篇,载《花城》91·3)中,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那位一生中惯于用网捕蟹且从未空网而归的蟹仙某日突发奇想,走火入魔,想出了用“六六六”药粉捕蟹的奇招,导演了一出“魔粉闹海"的惨剧。“那些一直泡在魔粉气氛中的海物,全都在劫难逃尸横遍野”,最后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蟹灾,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这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情节,很能表现南方的海的新的文化品格,透过这一事件引发的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思考,我们不难看到其中升腾的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在现今这个人口高度膨胀而自然资源日趋贫乏的时代,人对自然的索取如果没有一种必要的节制,人和自然没有一种默契,关于人类末日的寓言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现实;在邓刚的小说中,捕捞“五刺的海参”演变出的是海碰子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和英雄主义的赞歌,而在黄康俊的作品里,对海物的贪得无厌的捕取,却很可能是人类生存悲剧的开端。在南中国海中孕育出的这种新的文化品格与当今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认识存在一种整合趋势。


超越生活的世俗层面而追寻一种人生的终极关怀.使平庸的生活折射出些许哲理的光环.这一直是广东作家创作中不太注意从而使许多作品流于平庸的重要原因,黄康俊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形成一种后来居上的势头,正在于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往精神彼岸的桥梁,透过平庸无望的世俗生活,传来了遥远的天国的召唤。黄康俊小说中对生活世俗层面的超越,往往是通过来自外域宗教文化对本土文化的锲入而构成,《蟹岛》中的新加坡女人是这类外来宗教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乘着命运颠簸的小船来到雷州岛后,仍不改初衷.她那数十年如一日,风雨不改从不疏懒的圣事活动。并不仅仅是徒具形式的习惯性行为,而是一种企图通过宗教仪式进行的灵魂的自我救赎.因而即便是在青蟹群“鬼子围村似地从岛四周奔袭而来"引起全岛居民极度兴奋,物欲横流的时候,新加坡女人仍能超然物外,不为所动,在她看来,灵魂的救赎是比物欲的满足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黄康俊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对中国本土那种只图现世幸福,不求灵魂超渡的务实人生观的冲击,将会引发何种程度的震撼,但蟹仙的怆然死去和阿弟从母亲那里受到的人生启迪,却足以引起人们对南中国这片海域中发生的事情投以更大的关注了。外来宗教的影响引起的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领域的关注,也正是南方的海不同于北方的海的一个重要方面。
表现南方的海的神韵和她所代表的新的文化品格是黄康俊小说创作的特色,也是他的艺术追求。
黄康俊的新作《在外婆岛那边》(中篇,载《当代文坛报》1991.4-5)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算不上是最好的作品,但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它标志着黄康俊在小说艺术形式上新的尝试和探索以及新的人生思考。黄康俊以往的小说虽然也少不了一种扑朔迷离的色彩,但从来不像这部小说一样始终悬浮着一团难解的迷雾:那对除了他们的亲生母亲和他们自己之外谁也无法辨认的双孖仔(双胞胎)兄弟,当你越是想辨认他们时你越是无法辨认,这时你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小说的魅力由此产生了——穿透那团迷雾的冲动,逐渐转化为阅读的动力,也许到了最后,你还是难以解开那团谜,然而你却在解谜的过程中对自然、人生有了某种新的感悟。
大寿、细寿令人寻味不已的故事——他们那神秘的身世、嗜血如命的怪癖以及他们之间角色的错位与转换,表现了他们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不同文化内涵。

在自然层面上,他们和大自然有着一种神秘的血缘关系,他们与大海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与感应,他们几乎是靠着海蛇的血来维系生命的,他们和那两只棱皮海龟亲如兄弟,靠着它们,他们在平时海佬们行船都要绕开走的“臭海”里,一次又一次满载而归。在大海面前,他们活得自由舒展,无拘无束,他们不需要向谁证明、表白谁是谁,他们毫无做作地表现自己。
在社会层面里他们却老是在躲躲闪闪,互相叠合在另外一个的影子中,让人难以辨认,别说是那位眼力不济,满身迂气的私塾先生晚公,就连他们的父亲、家姐也从来没弄清楚,危机是在“安南妹”阿宜爱上大寿开始的,以往的瞒天过海的把戏在这场新的人生遭遇中不灵了,阿宜爱的是大寿,(为什么是大寿连阿宜自己也搞不清楚)尽管双孖仔们仍然尝试着玩了几回偷梁换柱的把戏,但社会道德对角色的规范和社会性所需要的人的自我约束力不允许他们再进行这种角色的互换,于是悲剧发生了……
在自然层面上,大寿、细寿作为人是真实可触的,而在社会层面中,他们却成了虚幻的影子,捉摸不定,难以辨认。这里我们不能不探究黄康俊的叙事动机了,这种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外力作用下引发的矛盾对立为何引起了作家深深的忧虑和关注?如果说黄康俊以往小说中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外部的冲突与谐调的话,那么黄康俊这部小说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人性内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和调节上来了。人的自然的生命活力何以在现实人生中处处受制约、挤迫,以致变得苍白虚弱?南海的涛声又一次把一种新的人生困惑摆到了作家和读者面前。
(《当代文坛报》1991年第4-5期合刊专号,附此文和黄康俊中篇小说《在外婆岛那边》同期发表)
[ 文 能 1958生,文学评论家。《花城》编辑部主任、《佛山文艺》主编。1985年在华西师大攻读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始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有《踏着太平洋文明浪潮走来的珠江文学》、《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接点上》等。其中《踏着太平洋文明浪潮走来的珠江文学》曾获1987年广东省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优秀作品奖,并被收入《新时期广东文学评论选》。]